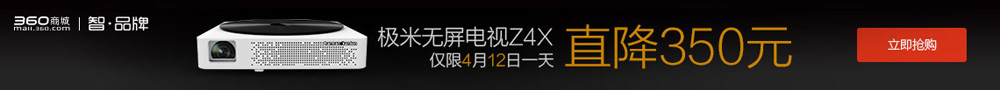一首《鄉(xiāng)愁》��,使余光中的名字傳遍華語文化圈����。每當炎黃子孫心中涌起家國之思、追問鄉(xiāng)關何處�,這位華發(fā)如雪的清癯老者就在人們的心頭揮之不去���。他已經(jīng)成為一個象征、一個標志���,他的離世似乎標志著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漸行漸遠。
讀過《鄉(xiāng)愁》的人很多��,但不知道真正理解《鄉(xiāng)愁》的人有多少���。如果沒有對于中華文化的深刻理解���,沒有對于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深刻體認,缺乏深沉的家國情懷和赤子之心���,恐怕很難領會到它的字字千鈞����、意象深沉��。一個古老的民族�����,在數(shù)千年歷史里承受著百轉千回的命運,歷盡光榮與夢想����、磨難與沉淪,卻始終堅韌如鋼�����,生生不息����。中華民族頑強而澎湃的生命力,源于獨一無二的中華文化���。她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無遠弗屆�����,哪怕是浪跡天涯����、漂泊四海的游子��,都能感受到她的召喚���,在這種文化母體里找到精神家園�,安頓自己的情感和心靈。
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�,1949年隨父母遷居香港,次年赴臺灣�。在創(chuàng)作《鄉(xiāng)愁》的時候,他已經(jīng)離開祖國大陸20多年了����。如筆者一樣生活在開放年代的后輩�����,已經(jīng)很難感受那種日夜煎熬的思鄉(xiāng)情切���,卻曾經(jīng)目睹長輩們久別重逢的肝腸寸斷和欣喜若狂����。筆者的家鄉(xiāng)是廣西最大的僑鄉(xiāng)����,兩位堂伯父都于1949年遷居臺灣。1989年��,他們第一次重返大陸。闊別四十年之后�����,白發(fā)蒼蒼的兄弟姐妹終得相見�。那種抱頭痛哭、大慟大喜的場景��,如今回想仍然歷歷在目�������;氐郊亦l(xiāng)之后,白天他們四處走動��,逐一尋訪故地故人��;晚上就和族人聚集在一起��,徹夜長談�。《鄉(xiāng)愁》這樣的詩歌���,飽含著他們這一代人多少思鄉(xiāng)之情��、望鄉(xiāng)之淚���。
如今����,借助發(fā)達的通信和交通����,“地球村”的居民早已“天涯若比鄰”。然而����,真正能把人們緊密地聯(lián)結在一起的�����,文化仍然是一條根本性紐帶�����。只要仍然傳承著共同的文化根脈���,共同體認著中華文化這一文化母體��,那么無論是一灣海峽�����,還是政治��、歷史和現(xiàn)實的阻隔���,都遮蔽不住人心思歸�����,都無法抵擋兩岸血濃于水的召喚�。
幾十年來��,兩岸交流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����。當囿于歷史和現(xiàn)實的種種羈絆,政治上還難有重大突破的時候�,兩岸文化的交流早就“輕舟已過萬重山”。鄧麗君的歌曲����、瓊瑤的小說����、侯孝賢的電影���,以及以綜藝節(jié)目為代表的臺灣電視節(jié)目�,都在大陸流行�。在嚴肅文化領域,臺灣的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����,包括余光中先生的文學創(chuàng)作,都在大陸獲得很高評價����,對大陸的相關領域產(chǎn)生影響。當然���,臺灣文化的源頭毫無疑問是跟祖國大陸共享的中華文化。哪怕是時髦新潮的周杰倫���,他低吟淺唱的《青花瓷》《發(fā)如雪》里面�,不也搖曳著風雅中華的一縷情絲嗎�����?
令人擔憂的是,隨著余光中這一代文化人的日漸離去����,當在大陸出生、遷居臺灣的一代人退場之后��,在臺灣出生成長的一代能否傳承好這份文脈���?他們還會像余光中先生那樣���,將血滲透在墨里,書寫自己對于家國故土和精神家園的熾烈情感嗎�?他們還會像筆者的堂伯父那樣,望鄉(xiāng)淚千行�、思鄉(xiāng)夢難平嗎?當他們偶然讀到“日暮鄉(xiāng)關何處是���?煙波江上使人愁”的時候�����,心里會有所觸動嗎��?或者說�����,他們還有鄉(xiāng)愁嗎����?
如果切斷了文化的根脈,斬斷了思戀的鄉(xiāng)愁�����,臺灣將何以搏擊太平洋的驚濤駭浪�,將何以安頓她漂泊的靈魂?這應該也是晚年余光中的關切和擔憂��。最近10多年�����,余光中一直反對島內(nèi)某些人降低高中教材中文言文比例的動議��,極力維護中華文化��。他說��,如果將文言文拋棄不用�,“我們將會變成‘沒有記憶的民族’”。余光中這種堅守的背后�����,既有拳拳的赤子情懷�����,也有深沉的文化憂思�。如今,他已離去�����,唯愿他留給我們的“鄉(xiāng)愁”可以照亮一條前路�����。